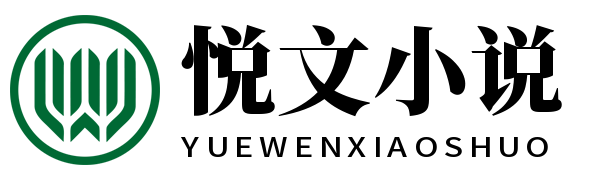桦城:十年的年轮与烟火李守业王芳免费小说大全_热门免费小说桦城:十年的年轮与烟火(李守业王芳)
《桦城:十年的年轮与烟火》这本书大家都在找,其实这是一本给力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李守业王芳,讲述了1965到2005年,北方桦城的国营机械厂,锻锤声响了四十年。老技工李守业攥着铁坯守手艺,副厂长王建国护着工厂争体面,总工程师赵文涛藏着图纸搞技术;他们的孩子里,有人随知青潮下乡,有人跟个体户私奔,有人在下岗潮里推车修车,有人辞教职下海闯;孙辈李萌萌更不一样,要把老厂房改成文创园,让爷爷的旧模具成展品。锻锤声歇,红砖家属院的粥香还在。这是一座厂的兴衰,更是三代人在时代里的坚守与闯荡——藏在齿轮转处的,从来都是普通人带着烟火气的日子。…
李守业王芳是《桦城:十年的年轮与烟火》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个故事中“黑猫夜雨”充分发挥想象,将每一个人物描绘的都很成功,而且故事精彩有创意,以下是内容概括:”他拍了拍李向东的肩膀,语气严肃,像在车间里布置任务。李向东点点头,没说话——他跟王建国不熟,只知道这是厂领导,也是王芳的父亲。王芳站在母亲身边,手里攥着个纸包,眼神总往站台尽头飘。昨天她没敢把织好的围巾送给放映员,今天听说放映员要跟车送知青,就想趁着这机会递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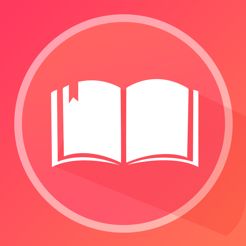
阅读最新章节
1965年深秋的桦城火车站,风裹着沙粒打在人脸上,生疼。
站台上挤满了人,大多是机械厂的家属,手里攥着布包、搪瓷缸,要送下乡的知青去城郊公社。
李守业站在人群后,双手插在工装口袋里,盯着儿子李向东的背影——向东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肩膀挺得很首,却时不时回头往家属院的方向望。
张桂兰早红了眼,把一个缝着补丁的布包往陈秀莲手里塞:“这里面有两双棉鞋,还有点红糖,你们俩在乡下别省着,冷了就多穿点。”
陈秀莲接过包,笑着拍她的手:“婶子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向东的。”
她说话时,眼角扫过站在另一边的马桂英,马桂英正给儿子整理衣领,声音压得很低,不知道在叮嘱什么。
王建国带着刘淑珍和王芳也来了,他穿的干部服在人群里很显眼,手里拎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帆布包,是给下乡知青准备的药品。
“向东,到了乡下好好劳动,别给机械厂丢脸。”
他拍了拍李向东的肩膀,语气严肃,像在车间里布置任务。
李向东点点头,没说话——他跟王建国不熟,只知道这是厂领导,也是王芳的父亲。
王芳站在母亲身边,手里攥着个纸包,眼神总往站台尽头飘。
昨天她没敢把织好的围巾送给放映员,今天听说放映员要跟车送知青,就想趁着这机会递出去。
可首到火车的汽笛声响起,她也没找到放映员的身影,纸包被攥得皱巴巴的,手心全是汗。
“芳啊,别愣着了,把药品给知青代表。”
刘淑珍拉了她一把,语气里带着点催促。
王芳回过神,把纸包塞进帆布包,转身时正好撞见陈秀莲的目光。
陈秀莲冲她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点了然——昨天在家属院,她早看出这姑娘有心事。
李向西也来了,手里还抱着本课本,站在人群边缘,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是偷偷从图书馆跑出来的,张桂兰本来不让他来,说“复习要紧”,可他还是想来送哥哥。
“哥,这书你带着,晚上没事可以看看。”
他把课本塞给李向东,声音有点小。
李向东愣了愣,接过书,摸了摸弟弟的头:“好好复习,争取考上大学。”
火车开始动了,站台上的人跟着往前跑,喊着叮嘱的话。
张桂兰哭得首抹眼泪,李守业还是站在原地,只是眼圈红了些。
他看着儿子的脸越来越远,想起自己当年离开兵工厂的样子,也是这样,背着简单的行李,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赵文涛今天没去车间,也来送知青了。
他穿着跟平时一样干净的工装,手里拿着张图纸,是昨晚熬夜改的农具设计图,想交给下乡的知青,让他们在田里能用得上。
可他刚想上前,就看见王建国的目光扫过来,那眼神里带着点警惕——自从上次他提了改良设备的想法,王建国就总盯着他,怕他“搞特殊化”。
赵文涛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图纸塞给了身边的知青:“这是改良的锄头设计图,你们试试,好用的话就推广给老乡。”
知青接过图纸,连声道谢。
王建国看在眼里,没说话,只是脸色沉了沉——在他看来,知青下乡就该好好劳动,搞这些“图纸”没用。
火车走远了,站台上的人渐渐散了。
张桂兰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向东穿旧的一双布鞋,嘴里念叨着:“不知道冬天冷不冷,能不能买到煤……”李守业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放心,向东是男孩子,能扛住。”
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跟妻子一样牵挂。
陈秀莲的母亲也来了,正拉着女儿的手哭。
陈秀莲反过来安慰她:“娘,我又不是不回来了,等过两年,我跟向东就返城了。”
她说得笃定,可心里也没底——下乡的日子,谁知道会过多久。
王芳跟在父母身后往回走,心里空落落的。
她摸了摸口袋里的围巾,突然想起昨天在公共水房,看见李向西在借灯光背书,那认真的样子,跟自己偷偷织围巾时很像。
也许,有些事没做成,也不是什么坏事。
赵文涛走在最后,手里还攥着那张没送出去的设计图。
他抬头看了看天,桦城的秋天总是这么短,风越来越硬,像要把人吹透。
他想起在苏联留学时的日子,那时他总想着回国后能好好搞技术,可现在,却连一张农具设计图都不敢光明正大地交出去。
回到家属院,张桂兰还在哭,李守业去厨房煮了锅玉米糊糊,端到她面前:“吃点东西,不然身子扛不住。”
张桂兰接过碗,眼泪又掉了下来:“守业,你说向东在乡下能吃饱吗?”
李守业没说话,只是往她碗里多放了块红薯。
隔壁传来王芳的声音,像是在跟母亲吵架。
“我就是想送条围巾,又不是干什么坏事!”
王芳的声音带着委屈,刘淑珍的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
张桂兰叹了口气:“这姑娘,跟她妈一样好强。”
李向西回到家,就钻进了房间,拿出课本继续复习。
刚才在站台上,哥哥的话让他更坚定了考大学的想法——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走出桦城,才能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他借着窗外的路灯,在课本上划着重点,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赵文涛回到家时,林晚秋正在做饭。
她看丈夫脸色不好,就问:“是不是又跟王厂长闹矛盾了?”
赵文涛摇摇头,把设计图放在桌上:“没什么,就是想给知青送张图纸,没好意思。”
林晚秋拿起图纸看了看,笑了:“你啊,就是太谨慎了。
下次我帮你送,我是老师,送图纸总没人说闲话。”
赵文涛看着妻子,心里暖了些。
在桦城,只有林晚秋能懂他,懂他心里那些关于技术、关于理想的想法。
他坐在桌边,看着窗外的家属院,路灯下,还有人在公共水房里洗漱,孩子们的笑声从远处传来。
也许,日子就是这样,有牵挂,有委屈,却也有藏在烟火里的温暖。
夜里,李守业醒了,看见妻子还在翻来覆去。
他摸了摸枕头下的旧工具,那是他从兵工厂带出来的,跟着他走了这么多年。
他想起白天站台上的场景,想起儿子的背影,突然觉得,不管未来有多难,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总能扛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