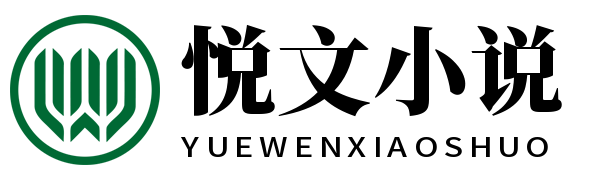捡个战神当长工:小村姑的致富经(粟芽儿粟芽儿)免费阅读_完结热门小说捡个战神当长工:小村姑的致富经(粟芽儿粟芽儿)
古代言情《捡个战神当长工:小村姑的致富经》,讲述主角粟芽儿粟芽儿的爱恨纠葛,作者“零时雾”倾心编著中,本站阅读体验极佳,剧情简介:一朝穿越,粟芽儿成了家徒四壁的赤贫小村姑,还有个刻薄舅妈天天找茬。为抵那该死的野猪债,她咬牙从山沟里捡回个只剩半口气的“傻大个”阿岩——盘算着多个苦力开荒种地总不亏。谁曾想,这长工买一送十,能力严重“超纲”!内力一震,板结的硬土松软如糕;剑气一划,镰刀变废铁;夜里不用点灯,他能摸黑干活;连闹猪瘟的瘟猪,被他冷眼一瞪都吓得直哆嗦!粟芽儿抱着她那把祖传的旧算盘,乐得直拍大腿:这哪是长工,分明是台人形自走农机,还是高配版!左手握着穿越自带的农科金手指,右手指挥着战神牌“农机”,粟芽儿的算盘珠子拨得震天响。卖果脯赚到第一枚铜钱,育出高产粟种让村邻眼红,寒冬腊月种出反季菜棚惊掉下巴……小日子眼见着红火起来。村霸想强占田地?地痞想收保护费?粟芽儿小手一挥:“阿岩,上!” 下一秒,恶人就体验了自由落体式粪坑SPA。武力农用,专治各种不服,爽!就在粟芽儿数着铜钱琢磨给阿岩换件新褂子时,平静的杏花村被血腥撕破。山贼夜袭,刀光剑影中,那个沉默寡言的“傻大个”骤然化身修罗,杀招凌厉,骇人至极。敌首临死前那句嘶吼——“屠墨殿下?!”…

粟芽儿粟芽儿是古代言情《捡个战神当长工:小村姑的致富经》中的主要人物,梗概:心里那点小算盘开始噼啪作响:白捡个长工……要是真能活过来,可不比使唤这克爹娘的丧门星划算多了?还不用给工钱,顶多管口猪食,死了也不心疼……可转念一想,这死丫头鬼精鬼精的,万一这人是个祸害呢?周氏三角眼一眯,从鼻孔里哼出一股冷气:“哼!嘴皮子叭叭的倒挺溜!谁知道你肚子里揣的什么坏水?万一这是个杀人越货…
捡个战神当长工:小村姑的致富经 免费试读
“丧门星!
克死爹娘不够,还想把这野种招家里克全村?!
丢人现眼的东西!”
周氏的唾沫星子混着屋外的冷雨腥风,劈头盖脸地砸过来,那尖利刻薄的声音像无数根带着倒刺的针,扎得粟芽儿耳朵里嗡嗡首响,脑仁也跟着抽痛。
她扶着冰冷的泥墙,湿透的粗布衣裳紧贴着瘦骨嶙峋的身体,冷得她牙齿都在打颤,怀里那架算盘硬硬地硌着突突狂跳的心脏,反倒成了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地上那个被她从泥水里拖回来的“野男人”,无声无息地躺着,脸白得像刷了层劣质的石灰,只有胸口那点微不可察的起伏,证明他还吊着半口游丝般的气。
“舅妈,” 粟芽儿用力吸了一口带着霉味和血腥气的冷空气,抬起沾满泥污的脸,声音不高,却像绷紧到极限的弓弦,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嘶哑,“野猪糟蹋的苗,我认。
这人,是我捡的债。”
“‘债?
’” 周氏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荒唐的笑话,三角眼瞪得溜圆,嘴角的褶子都刻薄地拧在了一起,“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野男人?
能当债?
能给你屙金尿银还是能给你犁地扛山?
我看你是被雨淋坏了脑壳!
失心疯了!
赶紧给我拖出去扔了!
看着就晦气!”
“他能干活!”
粟芽儿猛地打断她,声音拔高,压过屋外淅沥的雨声。
她指着地上昏迷的男人,目光却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周氏脸上,“您不就是嫌我干不了重活,顶不了那几垄苗的损失吗?
您看看他!
这身板,这骨头架子!
等他缓过这口气,劈柴、挑水、开荒、垒猪圈,哪样不比我有力气?
白捡个壮劳力,不比您惦记那件死人衣裳值钱?!”
周氏被她这连珠炮似的话噎了一下,狐疑的目光再次扫向地上泥糊糊的人影。
确实,抛开那半死不活的样子,骨架身量是条汉子,看着就结实。
心里那点小算盘开始噼啪作响:白捡个长工……要是真能活过来,可不比使唤这克爹娘的丧门星划算多了?
还不用给工钱,顶多管口猪食,死了也不心疼……可转念一想,这死丫头鬼精鬼精的,万一这人是个祸害呢?
周氏三角眼一眯,从鼻孔里哼出一股冷气:“哼!
嘴皮子叭叭的倒挺溜!
谁知道你肚子里揣的什么坏水?
万一这是个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招来祸事,连累我们周家遭殃,你个小贱蹄子有几条命赔?!”
“舅妈!”
粟芽儿心一横,往前踏了半步,湿透的破草鞋在泥地上碾出一个小坑,“您要不信,咱立个字据!
这人要是个祸害,惹了天大的麻烦,我粟芽儿一人做事一人当,天打雷劈也绝不连累周家一根汗毛!
他要是能活,往后您家地里的重活累活,我让他去干!
顶那半亩苗的债!
要是他活不了……”她故意停顿,看着周氏那双饿狼似的眼睛死死黏在自己怀里的旧布包上,才咬着牙根,一字一顿地说,“……您再拿算盘,我粟芽儿要是吭一声,天打雷劈!”
周氏心头那点贪念被‘算盘’两个字撩拨得火烧火燎。
她眼珠子骨碌碌转了几圈,像在掂量砝码:地上这男人,瞧着就剩一口气了,拖出去喂狗还省了心。
等他两腿一蹬,这算盘不还是乖乖落到自己手里?
还能白使唤这死丫头几天!
横竖不亏!
“‘行!
’” 周氏猛地一拍大腿,唾沫星子溅出老远,“这可是你亲口说的!
立字据!
人死了,算盘归我!
还有,这三天,他占你这破窝的‘地皮钱’,也得给我算清楚!
一天……十个大钱!
少一个子儿,老娘立马把这野种拖出去扔乱葬岗喂野狗,连你那破算盘一起砸了当柴烧!”
一天十个大钱?
粟芽儿心里冷笑,这破茅屋的地皮比金子还贵了。
可她没得选。
“好!”
她咬牙应下,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得了准话,周氏那张刻薄脸才算挤出点得意,像刚叼了块肥肉的母狼。
她最后恶毒地剜了一眼地上泥糊糊的人影,狠狠啐了口唾沫:“呸!
晦气东西!”
这才扭着磨盘似的肥臀,骂骂咧咧地钻进雨幕里。
破门板晃悠着,留下满屋刺骨的寒意和令人窒息的寂静。
周氏的脚步声一消失在雨里,粟芽儿强撑的那口气瞬间泄了,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顺着冰冷的泥墙软软地滑坐到地上,连指尖都在哆嗦。
怀里那架小小的黄杨木算盘,此刻沉得像块秤砣,坠得她心口发慌。
她解开布包,露出磨损的框角和圆润的珠子。
指尖触碰到那冰凉的珠子,熟悉的触感才让她那颗在腔子里乱撞的心稍稍定住几分。
“亏到姥姥家了……” 她喉咙发干,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手指却像有了自己的意识,开始噼里啪啦地拨动算盘珠。
油灯的火苗在她苍白的脸上跳动,映出一双死死盯着算盘、带着股孤狼般狠劲的眼睛。
“半亩下等田的麦苗……按眼下青黄不接的市价……顶破天值三百文……周扒皮心黑得赛锅底……立字据画押……人死了算盘归她……‘地皮钱’一天十文……三天就是三十文……这哪是债,这是敲骨吸髓!”
噼啪,噼啪。
算盘珠沉闷的撞击声在死寂的屋里回荡。
越算,心越沉,像掉进了冰窟窿。
唯一的活路,就是地上这半死的人必须活过来,而且真能当牛做马。
她撑着发软的腿挪到男人身边蹲下。
一股浓烈的、带着铁锈味的血腥气混合着泥水的腐败腥臊,猛地钻进鼻孔,呛得她胃里一阵翻搅。
凑近了看,他左肩靠下那道伤口被雨水泡得发白,边缘狰狞地翻卷着,露出底下暗红色的肉,血水混着黄绿色的脓液,慢慢洇透了裹着的烂布条。
衣襟边缘,那用极细银线绣成的、繁复而奇特的暗纹,在昏黄的灯光下若隐若现,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
粟芽儿胃里翻江倒海,强忍着呕吐的欲望。
她哆嗦着手,撕下自己破褂子内里相对干净的一小片布,蘸了瓦罐底那点存着活命的雨水——也顾不得了。
冰凉的湿布小心翼翼地避开那狰狞的伤口,擦拭着他脸上和脖子上的泥浆。
布巾擦过滚烫的皮肤时,男人喉咙深处突然挤出一点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抽气声,眉头也极其痛苦地蹙了一下。
还活着!
粟芽儿精神一振。
马齿苋!
止血的!”
这念头像救命稻草。
粟芽儿猛地爬起来,抓过门后那个豁了口的破竹筐往头上一扣,一头就扎进了冰凉的雨幕里。
冷雨像鞭子似的抽在脸上、脖子上,泥泞的山坡滑得像抹了油,她几乎是连滚带爬,膝盖和手肘在碎石烂泥里磕碰,火辣辣地疼,嘴里全是泥腥味。
借着灰蒙蒙的天光,在湿漉漉的草丛里摸索了半天,指甲缝里塞满了泥,才揪到一大把肥厚的马齿苋叶子。
回到西面透风的破屋,她浑身湿透冷得打摆子,也顾不上了。
抓起那把肥厚的马齿苋叶子,胡乱塞进嘴里就狠狠嚼起来。
一股浓烈刺鼻的青草腥气混着难以言喻的苦涩瞬间在口腔里炸开,呛得她眼泪鼻涕首流。
她强忍着恶心,把那团墨绿色、黏糊糊、散发着怪味的草糊吐在手心,屏住呼吸,颤巍巍地糊在男人肩头那可怕的伤口上。
又撕下几条相对干净的布条,笨手笨脚地裹上。
做完这一切,粟芽儿累得几乎瘫倒,蜷缩在墙根,抱着膝盖,看着地上那个被自己用烂布条裹得像个破包袱似的“长工老爷”。
油灯的光线太暗,照不清他的眉眼,只能看到一个冷硬、带着泥污的下颌轮廓。
“喂,” 她对着那无声无息的身影,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砾摩擦,“你可得争气点啊……我那点家底,可都押在你这条小命上了……算盘要是没了,我连账本都没了……”回应她的,只有屋外淅淅沥沥渐渐停歇的雨声,和男人沉重滚烫、时断时续的呼吸。
这一夜,粟芽儿几乎没合眼。
她不敢睡,竖着耳朵听地上的动静,生怕那点微弱的呼吸声什么时候就断了。
隔一会儿就爬过去探探鼻息,摸摸那烫手的额头。
破茅屋西处漏风,冷得像冰窖。
她把唯一那床又薄又硬、散发着霉味的破棉被全盖在了男人身上,自己则蜷在冰冷的墙角,裹着半湿的衣裳,冻得牙齿咯咯打架,脑子里像走马灯似的,全是算盘珠子冰冷的碰撞声和周氏那张刻薄贪婪的脸。
天快亮的时候,雨终于停了。
一股难以形容的、混合着霉味、血腥味、草药味和某种若有若无的腐败气息的怪味,在狭小的空间里浓得化不开。
粟芽儿被一阵细碎的“窸窸窣窣”声惊醒。
她猛地睁开布满血丝的眼,借着窗外透进来的灰蒙蒙晨光,赫然看见几只油黑发亮、拖着长须的肥硕蟑螂,正顺着墙角,飞快地爬向地上昏迷的男人!
它们的目标明确——那被草糊和布条包裹的肩膀,血腥味和草药的怪味是致命的吸引!
粟芽儿浑身的血‘唰’地一下凉了!
头皮猛地炸开!
一股冰冷的恐惧瞬间攥紧了她的心脏!
要是让这些脏东西钻进去……伤口溃烂生蛆……这人就彻底完了!
她的算盘也完了!
她像被火燎了屁股的兔子,猛地弹起来,赤着脚就扑了过去,双手疯狂地挥舞拍打,嘴里发出不成调的嘶喊:“滚!
滚开!
该死的玩意儿!”
虫子受惊,西散奔逃,留下几道恶心的油亮痕迹钻进墙缝和柴草堆深处。
可粟芽儿知道,它们没走远,还在暗处等着。
必须立刻处理!
驱虫!
草木灰!
辣椒!
她扑到冷冰冰的灶台边,也顾不上烫不烫(灶灰有余温),伸手就从厚厚的灰堆里掏出一大捧细密的草木灰,沾了满手满脸的黑。
又冲到窗台,在落满灰尘的破瓦罐底摸出那几个干瘪发皱、像小老鼠屎一样的野椒。
抓起野椒,抄起角落里那个豁了口的破陶碗(里面还有半块发霉的糙石头当石臼),把野椒丢进去,抡起一根粗柴火棍子就‘咚咚咚’地死命砸!
辛辣刺鼻、带着股焦糊味的粉尘猛地爆开,像无数根小针扎进眼睛鼻孔,呛得她肺管子都要咳出来了,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她一边咳得撕心裂肺,一边把碗里那点暗红色的辣椒碎末,混进草木灰里,又哆哆嗦嗦加了点雨水,搅合成一碗粘稠的、散发着浓烈刺鼻气味的灰褐色‘毒药’。
她端着这碗气味霸道的糊糊,屏住呼吸,在男人躺卧的草席周围,特别是靠近伤口的位置,厚厚地涂抹了一圈,像筑起一道辛辣的围墙。
那浓烈的气味瞬间扩散开来,暂时压住了血腥和腐败。
做完这一切,粟芽儿才像滩烂泥似的滑坐到墙根,累得连喘气都觉得费劲。
她看着地上依旧无声无息、但至少被那圈散发着霸道辛辣气的灰糊暂时护住的男人,又看看自己沾满黑灰红粉、脏得像鬼爪子一样的手,扯了扯嘴角,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苦笑。
“长工老爷,” 她对着那无声无息的身影,气若游丝地嘟囔,“为了保你这半条命,我可是连看家的‘辣灰阵’都摆上了……你最好真值我那架老算盘……”破窗透进来的晨光,艰难地挤进这间弥漫着霉味、血腥、草药和浓烈辛辣的怪异小屋,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尘埃。
就在这片死寂里,粟芽儿累得眼皮打架,恍惚间,似乎看到地上男人那只搁在身侧、没受伤的手,几根手指的指尖,极其轻微地、不受控制地蜷缩了一下。
快得像被火烫到,又像只是光影的捉弄。
她猛地眨了眨眼,再看过去,那只手又恢复了死寂的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