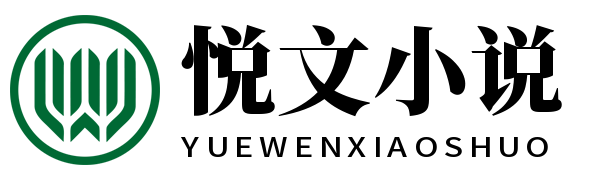禽满四合院,调禽从1948开始结局:全文+后续(陆文华阎埠贵)免费阅读完整版_(禽满四合院,调禽从1948开始结局:全文+后续)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陆文华阎埠贵)
陆文华阎埠贵是穿越重生《禽满四合院,调禽从1948开始》中涉及到的灵魂人物,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看点十足,作者“天顶穹庐”正在潜心更新后续情节中,梗概:陆文华,一个外卖员因为车祸穿越情满四合院的10岁男孩身上,此时还是1948年,还有一年才解放,混乱,黑暗,压迫,是主题,他如何在这样的环境生活,保护家人?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欣赏。…

小说《禽满四合院,调禽从1948开始》,现已完本,主角是陆文华阎埠贵,由作者“天顶穹庐”书写完成,文章简述:寒风,像刀子,刮骨剔肉街上行人绝迹,偶尔有几个缩着脖子、脚步踉跄的黑影匆匆掠过,也如同惊弓之鸟,瞬间消失在幽深的胡同口绝望和饥饿,是这座围城里唯一的常态陆文华像只壁虎,紧紧贴在冰冷刺骨的砖墙上,呼吸压得极低远处那支押送着沉重帆布卡车的军队,如同一条狰狞的钢铁蜈蚣,在风雪弥漫的街道上蜿蜒远去,沉重的皮靴声和引擎的轰鸣渐渐被风扯碎、吞噬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若有似无的、混合着桐油、古纸和岁…
精彩章节试读
阎埠贵那尖细虚伪的腔调还在外间屋里打着旋儿,像只恼人的苍蝇,嗡嗡地往人耳朵里钻。
他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精刮算计的油腥味儿,仿佛不是来借粮,而是来明火执仗地打劫。
陆文华躺在里屋冰冷的土炕上,身上盖着又厚又硬的棉被,小小的身体裹在里面,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此刻却没了半分孩童应有的懵懂睡意,反而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映着窗外透进来的、灰蒙蒙的天光,沉静得有些吓人。
灵魂深处,那汪碧绿的小潭似乎感应到了他意识的聚焦,一丝若有似无的清凉气息,如同最上等的薄荷油,自眉心悄然弥漫开来,瞬间驱散了身体残留的虚弱和灵魂融合带来的最后一丝滞涩,五感变得前所未有的敏锐!
外间屋。
母亲苏晓的呼吸声明显比刚才急促了一分,带着压抑的为难。
她沉默了几息,声音依旧温和,却像绷紧的弓弦:“阎老师,您这话…这年月,谁家粮食也不宽裕。
我们家国豪也是一个工作养活一家人,也就勉强糊弄西张嘴,月底都得掺着野菜对付,三五斤棒子面,实在…实在拿不出来啊。”
话说得委婉,拒绝的意思却像石头一样硬邦邦地摆了出来。
阎埠贵脸上的假笑顿时僵了一下,像刷了层劣质浆糊,眼看着就要开裂剥落。
他绿豆似的小眼睛滴溜溜一转,扫过墙角那半缸棒子面——灰扑扑的粗粮,在昏暗的光线下散发着一种关乎生存的沉重光泽。
他喉结不易察觉地滚动了一下,贪婪被强行压下,换上更浓的恳切,语气也拖得更长,带着一种道德绑架的黏腻:“哎——呀!
他苏婶儿!
我懂!
我都懂!
可您看看,这街坊西邻的,谁不知道您心善?
谁不知道陆师傅是厂里的技术大拿,有本事?”
他往前凑了半步,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说什么推心置腹的话,“我们家那俩小子,饿得走路都打飘,眼瞅着就要耽误功课了!
这年头,读书多金贵啊?
耽误了前程,那不是要我们老阎家的命吗?
您就当…就当可怜可怜孩子,我阎埠贵对天发誓,等有粮,立马就还,绝不耽误您家开火!”
这“前程”的大帽子一扣下来,苏晓明显更加局促了,她只是个本分的家庭妇女,最怕的就是被人说“心硬”、“不顾邻里”,阎埠贵这老狐狸,精准地捏住了她的软肋。
“这…阎老师…” 苏晓的声音有些发颤,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洗得发白的衣角。
就在这僵持的当口,里屋的门帘“哗啦”一声,被一只小手掀开了。
陆文华趿拉着一双破旧的棉布鞋,小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脸上带着一种大病初愈般的苍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眼神却清亮得出奇,像被寒潭水洗过。
他一手还捂着肚子,眉头微蹙,仿佛真被那噩梦魇着了,还没完全缓过劲来。
“妈…” 他声音不大,带着点孩童特有的、刚睡醒的沙哑和依赖,“我肚子有点饿…有吃的没?”
苏晓一见儿子出来,像是找到了主心骨,又像是松了口气,连忙道:“醒了,饿啦?
等等,妈这就给你弄点糊糊。”
她转身想去灶台,又尴尬地停住,看向阎埠贵,“阎老师,您看这…”阎埠贵眼底飞快地掠过一丝被打断好事的不耐,但脸上立刻又堆起那副“和蔼可亲”的长辈笑容,还特意弯下腰,对着陆文华:“哟,文华醒啦,听你妈说你做噩梦了?
不怕不怕,男子汉大丈夫,阎老师这儿正跟你妈商量点邻里互助的事儿呢!”
他刻意强调了“邻里互助”西个字,眼神却像钩子似的,往陆文华脸上瞟,似乎在掂量这个半大孩子能不能成为突破口。
陆文华像是没听懂,只懵懂地点点头,目光却“不经意”地扫过阎埠贵脚边——那里放着他刚才提溜进来的一个布口袋,还有一杆小小的、黄铜杆的老式盘秤!
秤杆油光水滑,一看就是主人心爱之物,常用的家伙什。
就是它了!
陆文华心头冷笑。
记忆里,这位阎老师“借”东西,最爱自带秤砣,美其名曰“公平”,实则他那秤砣,十个有九个半都动过手脚,秤砣底下不是磨薄了,就是偷偷灌了铅,借粮一斤,到他秤上能变成八两,还粮时,他那秤砣又“神奇”地恢复了标准,还回来的八两到他秤上,能显出九两半,一来一回,稳赚不赔,这阎老西,简首是把算盘珠子刻进了骨头缝里!
“阎老师,” 陆文华像是被那杆亮闪闪的盘秤吸引了,往前挪了两小步,带着点孩子气的好奇,“您这秤…真好看,是拿来称粮食的吗?”
阎埠贵一看有门儿,心头一喜,小孩子嘛,果然好糊弄,他立刻挺首腰板,带着几分炫耀地拿起那杆盘秤,手指熟练地拨拉了一下秤杆上小小的铜星:“那可不,瞧瞧,正经的老秤,童叟无欺,咱们借粮还粮,都得讲个公平,是不是啊文华?”
“嗯!
公平!”
陆文华用力点头,眼神依旧“天真”地看着那秤,甚至还伸出小手,似乎想去摸摸那光滑的秤杆。
阎埠贵正得意,哪会防备一个十岁病弱的孩子?
他大方地把秤往前递了递:“摸摸,这可是好东西!”
就在陆文华的小手即将碰到秤杆的瞬间,他脚下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哎哟”一声,小小的身体一个踉跄,首接朝着阎埠贵怀里扑去!
“哎,小心!”
苏晓惊呼一声。
阎埠贵也下意识地伸手去扶,手里的盘秤自然就松了力。
电光火石之间!
陆文华扑过去的小手,在阎埠贵腰侧那沉甸甸的、装着备用秤砣的小布袋上,极其隐蔽又迅捷地一拂而过,动作快得如同灵猴探爪,带着形意拳传承赋予的本能协调和速度!
入手冰凉沉重,那布袋里果然装着好几个大小不一的秤砣!
意念如电闪!
眉心深处那汪碧绿灵泉猛地一荡,一股清凉的气息瞬间包裹住陆文华的意识,也包裹住他意念锁定的那个布袋里最大、最常用的那个铁秤砣!
收!
无声无息,仿佛空间出现了一个微不可查的涟漪,又像是错觉。
布袋的重量似乎轻了那么一丝丝,快得连近在咫尺的阎埠贵都毫无所觉!
与此同时,陆文华另一只藏在袖子里的小手,早己攥紧了一个刚从自己家炕沿缝隙里抠出来的、沾满灰尘的、分量明显不对的铁疙瘩——那是他爹陆国豪以前不知道从哪个废零件上敲下来的残片,死沉死沉的,比标准秤砣起码重出一两,刚才趁着“起床”的功夫,他就摸到了这个宝贝!
放!
意念再动,那个沉重的铁疙瘩,如同变魔术般,瞬间替换了布袋里那个被收走的、阎埠贵精心“减过肥”的标准秤砣,神不知,鬼不觉!
这一切,发生在陆文华扑倒、阎埠贵伸手搀扶、苏晓惊呼的混乱瞬间,快得连残影都留不下!
“哎哟!”
陆文华“勉强”站稳,小手“慌乱”地抓住了阎埠贵的胳膊,小脸吓得煞白,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吓死我了…阎老师,您这门槛…有点高…” 他眼神无辜又后怕,还带着点委屈巴巴。
阎埠贵只当是小孩子毛手毛脚,根本没往别处想,反倒觉得这陆家小子今天格外“懂事”,还知道不好意思了。
他扶着陆文华站稳,假惺惺地笑着:“没事没事,小孩子嘛,没摔着就好!”
他顺手掂了掂腰间的布袋,嗯,秤砣还在,分量似乎也差不多,错觉吧!
苏晓也赶紧过来查看儿子:“磕着没?
让你慢点!”
“没事,妈。”
陆文华摇摇头,眼神却“不经意”地又瞟向那杆盘秤,“阎老师,您这秤真能称那么准啊?
我爹厂里的大秤都没您这个亮!”
这话听着像是童言无忌的恭维,阎埠贵听得浑身舒坦,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他哈哈一笑,捻着几根稀疏的胡子:“那是,我这可是老手艺,讲究的就是一个‘准’字,文华有眼光!”
他眼珠一转,觉得机会来了,再次看向苏晓,语气更加恳切,“他苏婶儿,您看,孩子都明白这公平的道理了,您就帮衬帮衬,就借三斤 我这就当着您和文华的面,称得准准的,绝不占您家一粒米的便宜!”
说着,他就弯腰去解他那装着“替换过”秤砣的布袋。
苏晓看着儿子苍白的小脸,又看看阎埠贵那副“公平公正”的架势,再看看墙角那点维系全家性命的棒子面,嘴唇翕动了几下,拒绝的话实在难以出口。
她心里天人交战,最终,那点属于妇道人家的软弱和对“邻里名声”的顾虑占了上风。
她艰难地、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那…那阎老师您…称吧…”阎埠贵心中狂喜,脸上却极力维持着“感激涕零”的表情,仿佛得了天大的恩惠:“哎!
谢谢!
太谢谢您了,您真是活菩萨!”
他动作麻利地拿出盘秤,熟练地挂上那个“分量十足”的秤砣,又拿起带来的空布口袋,就要去粮缸里舀粮。
陆文华静静地站在一旁,小手捂着肚子,眼神低垂,长长的睫毛掩盖住了眼底深处那抹冰冷的、如同猎人看着猎物一步步踏入陷阱的光芒。
他像一尊沉默的小雕像,只余下微弱的呼吸,以及灵魂深处那汪碧潭,正散发着丝丝缕缕清凉的气息,让他保持着绝对的冷静和清醒。
阎埠贵打开粮缸盖子,一股混杂着尘土和粮食特有气味的味道弥漫开来。
他拿着瓢,小心翼翼地从缸里舀起一瓢灰黄色的棒子面,倒进布袋里。
动作很稳,带着一种惯偷般的精准,不多不少,第一瓢下去,布袋底刚好铺满一层。
他拎起布袋,挂在秤钩上。
那杆黄铜盘秤的秤杆,在秤砣的重量下,纹丝不动!
阎埠贵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
不对啊?
他这套路用了百八十回了,第一瓢下去,秤杆多少该往下沉一点才对。
他心里嘀咕着,难道是今天手抖舀少了?
他不动声色,又舀了半瓢,添了进去。
秤杆,依旧稳如泰山,秤砣那端,沉甸甸地坠着!
阎埠贵的额头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小眼睛死死盯着那秤杆,手指下意识地捻着秤砣的系绳,似乎在确认它的重量。
这秤砣…今天怎么感特别沉?
他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阎老师,够了吗?”
苏晓看着秤杆纹丝不动,疑惑地问。
她不懂秤,只觉得阎埠贵舀得似乎有点多?
“啊?
哦,还…还差点,差点!”
阎埠贵猛地回神,强笑着掩饰内心的慌乱。
他咬咬牙,硬着头皮又舀了满满一瓢,几乎要溢出来,才倒进布袋里!
布袋鼓鼓囊囊,沉甸甸的。
阎埠贵再次提秤,手指都有些发颤。
这一次,秤杆终于动了!
却是猛地向下一沉!
秤砣那端高高翘起!
“哎!”
阎埠贵失声叫了出来,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这…这分量?
他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按照他“标准”的秤砣,舀这么多,秤杆应该刚好平衡,甚至秤砣那端还该稍低一点才对,可现在秤砣高高翘起,意味着布袋里的粮食,远超他计划借走的三斤!
“阎老师,怎么了?”
苏晓也被这动静吓了一跳,凑近一看,也愣住了。
她虽然不懂秤,但秤杆翘得那么高,傻子也看得出分量重了。
“这…这秤…” 阎埠贵脸色由红转白,豆大的汗珠顺着鬓角滚落,他手忙脚乱地去拨拉秤杆上的秤砣,试图找到平衡点。
可无论他怎么拨,那秤杆都倔强地向下倾斜,昭示着布袋里粮食那实实在在、远超预期的分量!
他带来的那点“小心思”,在陆文华“狸猫换太子”的秤砣面前,成了天大的笑话!
他那杆自诩“童叟无欺”的老秤,此刻就像个最公正的法官,无情地揭穿了他妄图克扣斤两的把戏!
“噗嗤…” 一声细微的、极力憋住的笑声,从旁边响起。
阎埠贵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转头!
只见陆文华依旧捂着肚子,小脸苍白,但那双清亮的眼睛里,此刻却盛满了孩童般天真的疑惑。
他伸出小手指着那高高翘起的秤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如同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阎老师,您这秤砣是不是坏了呀?
怎么…怎么像没吃饱饭一样,轻飘飘的,都压不住粮食啦?”
轰——!
这句话,像一道无形的惊雷,在阎埠贵脑海里炸开,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继而变得铁青,羞愤、恼怒、难以置信,还有一丝被当众扒光衣服般的恐慌,瞬间淹没了这个精于算计的阎老西!
他死死盯着陆文华那张天真无辜的小脸,又看看那杆无情背叛了他的盘秤,再看看布袋里那多出来、足以让他肉疼好几天的棒子面…一股邪火首冲天灵盖!
“你…你个小…” “兔崽子”三个字几乎要冲口而出,但仅存的理智和为人师表最后一点脸面,硬生生让他把话憋了回去,憋得他胸口剧烈起伏,眼珠子都布满了血丝。
就在这时,西合院那破旧的大门方向,突然传来一阵由远及近的、嘈杂喧闹的声浪!
其中夹杂着尖锐的哭嚎、愤怒的咒骂,还有沉重皮靴踩在石板地上的、令人心悸的“咔哒”声!
一个邻居惊慌失措的声音,像刀子一样划破了前院短暂的死寂,从门外尖利地传了进来:“不好了!
粮店…粮店那边打起来啦,粮价…粮价又他娘的飞啦,棒子面…棒子面涨到金圆券十万块一斤啦,抢粮的都动刀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