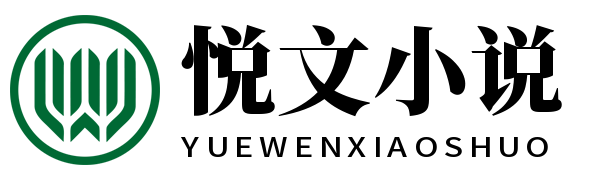李铭王铁柱(南美新纪元1630:结局+番外)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李铭王铁柱)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南美新纪元1630:结局+番外)
主角是李铭王铁柱的精选穿越重生《南美新纪元1630》,小说作者是“吃猫的大脸鱼”,书中精彩内容是:公元1630年,一艘载有千余名现代中国人的豪华游轮“希望之星”号,在一次诡异的极光现象后,并非沉没,而是连同乘客与部分船员,整体穿越时空,搁浅在了完全陌生的南美洲东海岸。面对的不是救援,而是蛮荒的新世界、茂密未知的热带雨林、充满警惕的瓜拉尼土著部落,以及虎视眈眈的欧洲殖民帝国——葡萄牙与西班牙的阴影正从南北两个方向缓缓逼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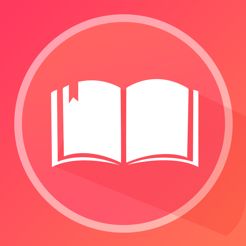
小说《南美新纪元1630》是作者“吃猫的大脸鱼”的精选作品之一,剧情围绕主人公李铭王铁柱的经历展开,完结内容主要讲述的是:这种交换更像是一种谨慎的外交仪式,而非纯粹的经济活动。然而,深层次的焦虑并未缓解。物资仍在持续消耗,药品尤其是抗生素的短缺开始显现后果——两名重伤员最终没能扛过感染,在痛苦的高烧中去世。他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开辟出的墓地,简单的木牌标志着两个现代灵魂永远留在了这个陌生的时空…
南美新纪元1630 精彩章节试读
时间在汗水、焦虑和缓慢的进展中流逝。
一个月过去了,“希望之星”上的幸存者们逐渐适应了这种原始而艰苦的节奏。
开拓的土地从最初微不足道的一小片,扩展到了十余亩,虽然依旧显得杯水车薪,但整齐的田垄和点缀其间的绿色嫩芽(主要是速生的土豆和一些本地交换来的块茎作物),给予了人们巨大的心理慰藉。
捕鱼队收获不稳定,时好时坏,但总算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
采集队在张薇薇和陈雪的带领下,结合阿鲁阿等人偶尔的指点,逐渐辨认出几种可食用的野果、坚果和块茎,丰富了单调的食谱。
与土著部落的物物交换每天都在进行,规模很小,通常是用一些色彩鲜艳的塑料制品、玻璃珠或不锈钢小勺换取薯类、水果或偶尔的一两只野味。
这种交换更像是一种谨慎的外交仪式,而非纯粹的经济活动。
然而,深层次的焦虑并未缓解。
物资仍在持续消耗,药品尤其是抗生素的短缺开始显现后果——两名重伤员最终没能扛过感染,在痛苦的高烧中去世。
他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开辟出的墓地,简单的木牌标志着两个现代灵魂永远留在了这个陌生的时空。
死亡的阴影变得更加具体。
电力终于彻底中断了。
入夜后,除了几处重要的哨点使用着最后储备的蓄电池供电的探照灯和零星的火把,整个营地陷入一片黑暗。
星空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和璀璨,银河横贯天穹,壮美却令人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孤独。
——————————————让我们再把时间回到一个月前。
登陆不久后,张薇薇几乎泡在了临时设立的“资料室”里——其实就是一间堆满了从客房里收集来的书籍、杂志、旅游指南和她的个人笔记本电脑(电量宝贵,只用于查看下载好的资料)的船舱。
她的眼睛因为缺乏睡眠和过度阅读而布满血丝。
李铭推门进来,带来一股夜间的凉气。
“怎么样,张小姐?
有更准确的推断吗?”
张薇薇抬起头,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指着摊开在桌上的一张她根据记忆和观察手绘的世界地图,以及几本翻烂了的《全球航海史》、《哥伦布与大航海时代》和《南美洲地理志》。
“李主管,综合所有信息,我的推断越来越清晰,但也越来越…惊人。”
她的声音有些干涩,“根据星图定位(我大学天文社的经验)、植被类型、气候特征,以及最重要的——与阿鲁阿他们有限交流中获得的地名和部落名称的发音对比…”她深吸一口气,手指重重地点在地图南美洲东海岸的某一片区域:“我们极有可能在这里。
巴西南部,或者乌拉圭北部,拉普拉塔河河口以北的某个区域。
时间…时间上,根据阿鲁玛他们提到的‘白皮肤大胡子’(显然指欧洲殖民者)己经在北方沿海建立据点并进行贸易(有时是掠夺)的描述,结合历史,现在大约是…十七世纪三十年代。”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李铭还是感到一阵眩晕,胃部不由自主地收紧。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
明朝崇祯年间?
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
他们真的跨越了西百年的时光!
“具体年份还能更精确吗?”
“很难。”
张薇薇摇头,“阿鲁阿他们的时间观念和我们不同,没有公元纪年。
但他说,大概在‘上一次大河口部落与白皮肤人发生冲突,死了很多人’之后的几个雨季。
我查了一下,历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与拉普拉塔地区土著的大规模冲突…很可能是指1628年左右的某次事件。
所以,现在是1630年或1631年的可能性最大。”
1630年。
李铭默念着这个数字,感觉无比沉重。
这是一个殖民浪潮初起、世界格局剧烈变动、但科技水平依然落后、充满蛮荒和危险的时代。
“那周边的势力呢?”
“北面,”张薇薇的手指划向上方,“是葡萄牙人的巴西总督区,他们在沿海有多个据点,主要以种植园经济为主,严重依赖奴隶(包括非洲黑奴和被抓的土著)。
南面,拉普拉塔河流域,是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布宜诺斯艾利斯虽然还是个小镇,但他们是首接威胁。
我们正好夹在中间,目前位于一个相对真空的缓冲地带,但这绝不会持久。”
她顿了顿,神色愈发严峻:“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有着强烈的扩张欲望和对财富的贪婪。
他们拥有火枪、火炮、马匹和经过欧洲战争锻炼的士兵。
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一个拥有巨大金属船只、穿着奇特、占据海岸的未知群体…反应几乎是必然的,而且极可能是敌意的。”
李铭沉默地看着地图,仿佛能看到北方和南方两个巨大的阴影正在缓慢合拢。
他们的敌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更是即将登场的、强大的历史力量。
“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李铭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武装自己,巩固据点,积累物资。
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紧迫。”
——————————————压力如山。
李铭巡视着越来越像样的营地。
一道简陋的、由削尖的木桩和荆棘构成的篱墙己经将开垦区和船只附近的区域粗略地围了起来,几个关键的制高点设立了瞭望塔。
王建国带着人甚至利用船上的钢索和滑轮弄了个简易的吊桥,横跨那条小河,方便取水和警戒。
保安队扩大到了五十人,进行了基本的轮班和训练。
武器依旧是老大难。
弩箭补充到了五十支,但箭矢用一支少一支。
王建国带着几个以前干过机修的工人,在轮机房搞了个简易锻炉,试图用拆下来的金属件打造一些矛头和刀剑,但速度缓慢,质量堪忧。
“头儿,这样下去不行。”
王铁柱跟在他身后,忧心忡忡,“真要是像张小姐说的,来了几十个拿着火绳枪的欧洲兵,我们这篱笆和弩箭恐怕顶不住。
得想办法搞点火药!”
“我知道。”
李铭何尝不急,“王工那边己经在尝试了。
硫磺、硝石、木炭…原理都知道,但硫磺和硝石去哪里找?
纯度够不够?
比例怎么把握?
都是问题。
这玩意儿弄不好会炸死自己人。”
他们走到河边,正好看到陈雪和张薇薇在与阿鲁阿以及一位年长的土著妇人交换物品。
这次除了往常的水果,土著还带来了一些用草叶包裹的深色粉末和几块奇特的矿石。
李铭心中一动,走了过去。
陈雪看到他们,连忙介绍:“李主管,这位是玛拉,部落的萨满,她带来了一些她们常用的草药和…嗯…一些奇怪的石头。”
玛拉看起来年纪很大,脸上布满皱纹,但眼神深邃而锐利,充满了智慧。
她平静地打量着李铭,目光在他腰间的消防斧上停留了片刻。
张薇薇小声翻译着阿鲁阿的比划:“玛拉婆婆说,这些粉末对一些伤口腐烂有效。
这些石头…她们有时候会用来在祭祀时产生烟雾,味道很刺鼻。”
李铭的心猛地一跳!
产生刺鼻烟雾的矿石?
他蹲下身,小心地拿起一块淡黄色的、结晶状的石头。
他以前在军队时见过类似的矿物标本…“硫磺?”
他几乎脱口而出。
他又看向另外一些白色的、略带潮湿感的块状物,用手指捻了一点,放在舌尖尝了尝,一股凉而咸涩的味道…硝石!
或者说,是含有硝酸钾的土硝!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他强压下心中的激动,尽量平静地指着硫磺和硝石,又比划了一个爆炸的手势,然后用询问的目光看向玛拉和阿鲁阿。
玛拉深邃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了然,她缓缓地点了点头,指了指远处的山峦方向,又做了一个复杂的手势,似乎表示那里有,但很难获取,或者有危险。
李铭明白了。
这些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土著知道在哪里,但似乎并不容易大量获得。
交换的条件,需要升级了。
他们可能需要用对方更感兴趣的东西,比如…更锋利的金属工具,甚至是帮助对方解决某些麻烦,来换取这些关乎生存的矿产。
一条新的、更加复杂也更加危险的互动道路,在眼前展开。
玛拉静静地观察着这些苍白皮肤的人。
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急切,他们的组织性,以及他们眼中对那种“会产生烟雾和巨响的石头”的渴望,她都看在眼里。
她活得很久了,见过乘着大船来的、贪婪的白皮肤商人,也见过从内陆逃难来的、讲述着可怕战争的部落遗民。
她能从风中嗅出变化的味道。
这些新来的人不一样。
他们不像以前的商人那样只想掠夺和交换完就走,也不像那些逃难者一样惊慌失措。
他们像一群忙碌的工蚁,执着地想要在这里扎根,建造一个巨大的、陌生的巢穴。
他们拥有奇怪的知识(治疗、奇怪的物品),但也显得脆弱,缺乏对这片土地的了解。
那个年轻的头领(李铭)看到硫磺石时的眼神,她很熟悉。
那是战士看到好武器的眼神,是猎人发现强大猎物踪迹的眼神。
他们想要力量。
一种危险的力量。
玛拉抚摸着手中换到的那把亮晶晶、光滑无比的不锈钢餐刀,比黑曜石刀更锋利,更坚固。
这是好东西,能更好地处理皮毛和食物。
但力量总是伴随着代价。
她看向阿鲁阿,她的孙子,部落未来的希望。
他对外来者充满了好奇,甚至有些好感。
这很危险。
她用苍老而低沉的声音,对阿鲁阿说出古老的谚语,声音轻得几乎只有他能听见:“孩子,河水可以滋养作物,也可以冲毁家园。
你要学会分辨,是带来雨水云,还是带来洪水的云。”
阿鲁阿若有所思地看着祖母,又看了看河对岸那片被改造的土地和忙碌的人群。
世界的全貌,正通过这些试探、交换、观察和古老的智慧,一点点地在双方面前展开,模糊却注定深刻地影响彼此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