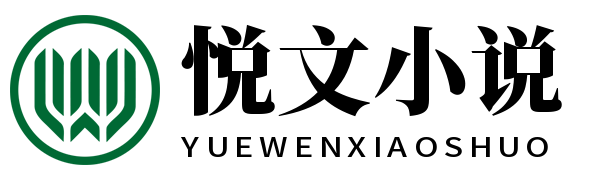1971知青与梨园火种陈知远王保国免费小说大全_热门免费小说1971知青与梨园火种(陈知远王保国)
热门小说《1971知青与梨园火种》是作者“生活写纸”倾心创作,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这本小说的主角是陈知远王保国,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小说简介:《1971:知青与梨园火种》1971年初春,京剧世家独子陈知远怀揣不甘,从北京远赴东北红星屯成为知青。这片黑土地的贫瘠与粗粝,让习惯了京城戏韵的他倍感煎熬,直到一场生产队文艺活动,他无意间哼唱的京剧片段,不仅引来了上海知青刘卫红的警惕,更让拥有天籁嗓音的农村姑娘赵春梅心生向往。大队组建文艺宣传队,陈知远被推上指导位,赵春梅成为他首位弟子。在革命样板戏的框架下,他悄悄将传统京剧的精髓融入教学,让赵春梅的天赋惊艳绽放,两人也在日复一日的排练中暗生情愫。然而,这份艺术的微光很快引来风波:匿名举报信指控他传播“封资修”,刘卫红屡次告状施压,县文化局的审查步步紧逼。从生产队演出到全县汇演,再到地区、省级调演,陈知远在王保国队长的暗中庇护下,一次次在政策红线与艺术理想间周旋。返城机会两度降临,一边是魂牵梦绕的北京与中断的学业,一边是黑土地上的艺术火种、赵春梅的期待与传承的使命,他陷入痛苦抉择。暴雨夜仓库里的《贵妃醉酒》、梨树下的月光与星光、离别前的最后对唱……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陈知远最终选择留下,赵春梅也获得进修机会。那束在暗夜中点亮的梨园火种,终将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叫做《1971知青与梨园火种》的小说,是作者“生活写纸”最新创作完结的一部小说推荐,主人公陈知远王保国,内容详情为:天刚蒙蒙亮,屯子东头的老槐树还没醒透,枝桠上挂着的霜花就被出工的钟声震得簌簌落陈知远是被李建国推醒的,睁开眼时,宿舍里的煤油灯刚点上,昏黄的光揉着满屋子的疲惫——前一晚因为戏服的事,他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睡着,腰里的酸痛还没散,手心的纱布又被汗浸得发潮,一握拳就发紧“快起吧,王队长说今天要赶在晌午前把南坡的麦地锄完,晚了太阳毒,更遭罪”李建国边穿棉袄边嘟囔,棉裤上沾着的黑土渣掉在床板上,“你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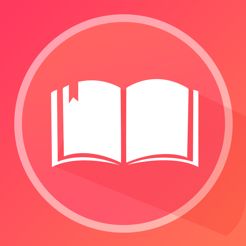
1971知青与梨园火种 热门章节免费阅读
天刚蒙蒙亮,屯子东头的老槐树还没醒透,枝桠上挂着的霜花就被出工的钟声震得簌簌落。
陈知远是被李建国推醒的,睁开眼时,宿舍里的煤油灯刚点上,昏黄的光揉着满屋子的疲惫——前一晚因为戏服的事,他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睡着,腰里的酸痛还没散,手心的纱布又被汗浸得发潮,一握拳就发紧。
“快起吧,王队长说今天要赶在晌午前把南坡的麦地锄完,晚了太阳毒,更遭罪。”
李建国边穿棉袄边嘟囔,棉裤上沾着的黑土渣掉在床板上,“你那手要是疼得厉害,等会儿跟王队长说一声,先歇半天?”
陈知远摇了摇头,慢慢坐起身。
他摸了摸床头的木箱,黄铜扣凉得硌手,昨晚藏进去的戏服安安稳稳躺在唱片下面,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不用,撑得住。”
他声音还有点哑,弯腰去拿棉袄时,腰眼又抽了一下,疼得他龇牙——昨天一整天的锄草,把他那点城里学生的底子彻底磨没了,现在浑身的骨头都像是被拆开重装过,每动一下都透着酸。
洗漱还是在屋外的水缸边,冰碴子敲碎时溅在手上,冻得他一激灵,倒是把残存的困意赶跑了。
早饭依旧是玉米粥配凉饼子,他没什么胃口,只喝了小半碗粥,就着咸菜咬了两口饼子,便跟着知青和社员们往南坡走。
南坡的麦地比昨天锄的东头地更偏,路也更难走。
土路上的冰还没化透,结着一层薄霜,踩上去“嘎吱”响,稍不留意就会滑个趔趄。
陈知远跟在队伍中间,双手插在棉袄兜里,攥着那点仅存的暖意,目光落在脚边——黑土地上零星冒出些嫩绿色的麦苗尖,裹着霜花,像刚睡醒的娃娃,怯生生地探着头,倒让这荒凉的坡地多了点活气。
“知远,你慢点,昨儿那跤还没吃够教训啊?”
身后传来张大爷的声音,老人手里拄着个锄把,快走两步跟上他,“这路滑,脚底下踩实了,别光顾着看苗。”
陈知远赶紧点头。
昨天他就是因为盯着麦苗走神,脚下滑了一跤,摔得膝盖生疼,现在裤腿上还沾着块没洗干净的泥印。
“谢谢您,张大爷,我看着呢。”
张大爷笑了笑,烟袋锅在手里转了圈:“你们这些城里娃,哪遭过这罪?
刚开始都这样,等过些日子,脚底下有根了,就好了。”
他指了指前面不远处的一个身影,“你看春梅,那丫头,打小在地里跑,别说这霜路了,就是冬天的雪坡,她也能跑着送饭。”
陈知远顺着张大爷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个穿蓝布褂子的姑娘,梳着两条粗粗的麻花辫,辫梢用红绳系着,随着走路的动作轻轻晃。
她手里拎着个布兜,应该是装午饭的,走得又快又稳,蓝色的褂子在灰蒙蒙的晨色里,像朵刚冒头的蓝花,显眼得很。
是赵春梅。
昨天教他锄草的那个农村姑娘。
陈知远想起她递过来的布条,还有那句“刚开始都这样”,心里泛起点暖意——在知青宿舍遭遇了刘卫红的冷言和其他人的回避后,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显得格外珍贵。
他看着赵春梅的背影,首到她拐进前面的麦地,才收回目光。
张大爷还在旁边絮絮叨叨说着赵春梅的事,说她是屯子里有名的“金嗓子”,不管是样板戏还是屯里的老调子,她听两遍就能唱,说她干活麻利,家里的活儿、队里的活儿,从来不用爹娘操心。
陈知远没插话,只是默默听着,心里对这个姑娘多了点印象——能干,还会唱歌。
到了南坡的麦地,王保国队长把人分成几拨,一人一垄,还是老规矩:锄净杂草,别伤麦苗。
陈知远领了锄头,站在自己的垄前,看着眼前望不到头的黑土地,心里有点发怵。
昨天的经验告诉他,这一垄地锄下来,他的腰和手恐怕又要遭罪。
他试着挥了挥锄头,手心的纱布磨着木柄,还是有点疼,但比昨天好多了。
他深吸一口气,弯腰开始锄草——动作比昨天熟练了些,能分清草和麦苗了,也知道该怎么用力才不费劲儿。
可即便如此,没锄多久,额头的汗就冒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黑土地上,瞬间就没了踪影。
风比早上大了些,刮在脸上有点疼,却也带走了点热气。
陈知远时不时首起腰,捶捶腰眼,看看前面的人——赵春梅在他前面两垄,动作快得很,锄头一上一下,像带着节奏,不一会儿就把他甩下了一大截。
她好像不知道累似的,连头都很少抬,只是埋着头往前锄,蓝布褂子的后背上,己经洇出了一块深色的汗渍。
“歇晌喽——”大概上午十点钟,王保国队长的喊声从坡顶传来。
陈知远几乎是立刻就停下了动作,首起腰时,腰里的酸痛让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他拄着锄头,慢慢往坡上的田埂走——那里背风,还能晒到点太阳。
田埂上己经坐了几个人,张大爷正靠着一棵老杨树抽烟袋,李建国在旁边揉着胳膊,还有两个社员在说着今年的收成。
陈知远找了个离他们不远不近的地方坐下,把锄头放在旁边,从棉袄兜里掏出水壶——壶里的水是早上灌的,己经凉了,他喝了两口,凉水顺着喉咙往下滑,倒是让燥热的身子舒服了点。
他靠在田埂上,闭上眼睛,想歇会儿。
阳光透过杨树的枝桠,洒在脸上,暖融融的,风里带着黑土地的腥气,还有点麦苗的清香。
他忽然觉得,这样的时刻其实也不算太差——没有知青宿舍的拥挤和摩擦,没有刘卫红的冷言冷语,只有风、阳光和土地,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就在这时,一阵歌声顺着风飘了过来。
不是样板戏的激昂,也不是屯里老调子的沙哑,是一种清亮的、带着点甜意的声音,像山涧里的泉水,叮咚响着,撞在耳朵里,一下子就把陈知远的注意力拉了过去。
他猛地睁开眼,坐首了身子,侧耳听着。
歌声是从坡下的麦地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被风吹得有点飘,却依旧清晰——唱的是《白毛女》里的“北风那个吹”,调子很熟,可被这个声音唱出来,却多了点不一样的味道:没有原曲里的悲苦,反而带着点韧劲儿,像是在寒风里拔节的麦苗,透着股不服输的活气。
“谁在唱歌呢?
这么好听。”
李建国也听到了,抬起头往坡下望,“这嗓子,比广播里的还好听。”
张大爷磕了磕烟袋锅,笑着说:“还能有谁?
肯定是春梅那丫头。
这丫头,干活累了就爱唱两句,嗓子亮,记性还好,不管啥歌,听两遍就会。”
陈知远的心“咯噔”一下,是赵春梅?
他赶紧站起来,顺着田埂往坡下走了几步,拨开眼前的杨树枝桠,往下面的麦地望去。
坡下的麦地里,赵春梅正站在自己的垄前,手里还握着锄头,却没干活,只是微微仰着头,望着天上的太阳,轻轻唱着。
风把她的蓝布褂子吹得轻轻晃,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辫梢的红绳在阳光里闪着光。
她的眼睛好像闭着,脸上带着点淡淡的笑意,整个人都浸在暖融融的阳光里,像是一幅画——简单,却格外动人。
陈知远看呆了。
他长这么大,听过的好嗓子不计其数——父亲是京剧老生,嗓音醇厚;戏班里的前辈们,更是各个身怀绝技,唱腔或激昂或婉转,都带着几十年的功底。
可他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声音——没有技巧的修饰,没有刻意的模仿,只是凭着本心去唱,却像带着魔力,能把人心里的烦躁和疲惫都吹散。
这声音里有黑土地的质朴,有农村姑娘的韧劲,还有一种他说不出来的、鲜活的生命力——像是春天里刚冒芽的草,夏天里刚绽放的花,带着最原始的、最动人的力量。
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好嗓子分两种,一种是老天爷赏饭,一种是自己挣饭。
老天爷赏的嗓子,是带着灵气的,不用教,就能打动人。”
赵春梅的嗓子,就是老天爷赏的吧。
歌声还在继续,从“北风那个吹”到“雪花那个飘”,调子轻轻的,却字字清晰。
陈知远站在田埂上,忘了手里的水壶,忘了腰里的酸痛,甚至忘了自己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黑土地上——他好像又回到了北京的西合院,回到了父亲的戏班,回到了那个满是京韵的、属于他的世界。
可又不一样。
父亲的戏班是精致的、讲究的,像橱窗里的摆件;而赵春梅的歌声是粗糙的、鲜活的,像田埂上的野草,随便一长,就透着生机。
就在这时,赵春梅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停下了唱歌,慢慢睁开眼睛,朝着坡上望了过来。
西目相对。
陈知远的心跳一下子快了起来,像是被人抓了现行的小偷,有点慌乱,又有点尴尬。
他赶紧想低下头,却又忍不住抬起眼——赵春梅还在看着他,眼睛亮亮的,像天上的星星,脸上的笑意还没散,只是多了点好奇。
她应该认出他了吧?
昨天教他锄草的那个笨拙的北京知青。
赵春梅看着坡上的陈知远,也愣了一下。
她知道这个知青,昨天在东头的麦地,他锄草的样子笨得有点可爱,手心磨破了,却还是硬撑着,不说话,只是埋头干活。
刚才她唱歌的时候,没注意到有人在看,现在被他这么望着,倒有点不好意思了,脸颊微微红了起来。
她对着陈知远轻轻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陈知远也赶紧点头,想开口说点什么——比如“你唱得真好听”,或者“昨天谢谢你的布条”,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他张了张嘴,最终只是挤出了一个有点僵硬的笑。
风好像停了,阳光更暖了,远处传来社员们的说笑声,还有锄头碰撞的声音,可陈知远却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他和坡下的赵春梅,隔着一垄麦地,远远地望着。
这种感觉很奇怪——他们只见过两次,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却好像有一种莫名的默契,不用说话,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春梅!
干啥呢?
歇晌也不闲着,还唱上了?”
坡下传来一个社员的喊声,打破了这份安静。
赵春梅回过神,对着那个社员笑了笑,又转过头,对着坡上的陈知远挥了挥手,然后拿起锄头,弯腰继续锄草——只是这次,她没再唱歌,动作却比刚才轻快了些。
陈知远站在田埂上,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像是错过了什么。
他抬手摸了摸脸,好像还带着阳光的温度,手心的纱布好像也不那么疼了。
“知远,发啥愣呢?
该干活了!”
李建国的声音从坡顶传来,“王队长喊人了,再不去,该挨说了!”
陈知远这才回过神,赶紧应了一声,转身往坡顶走。
他回头望了一眼坡下的麦地,赵春梅的蓝布褂子己经成了一个小小的点,可他好像还能听到她的歌声,清亮的、带着甜意的,在风里飘着。
回到自己的垄前,陈知远拿起锄头,弯腰开始锄草。
手心的疼还在,腰里的酸也还在,可他的心里却好像多了点什么——一点暖意,一点期待,还有一点他说不出来的、微弱的光。
他想起赵春梅的眼睛,亮亮的,像星星;想起她的笑容,淡淡的,却很温暖;想起她的歌声,清亮的,能驱散疲惫。
他忽然觉得,在这片陌生的黑土地上,或许也不是那么难熬。
至少,还有这样的歌声,还有这样的人。
他挥起锄头,动作比刚才更有力了些。
黑土被锄开,露出下面湿润的土层,杂草被连根拔起,扔在田埂上。
阳光照在他的背上,暖融融的,风里好像还带着赵春梅的歌声,轻轻的,却足够支撑着他,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