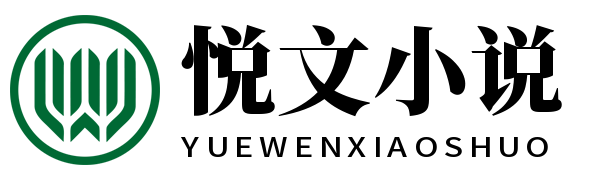最热门小说排行榜人间烟火与法治之光(抖音热门)_人间烟火与法治之光抖音热门小说完整版
抖音热门是现代言情《人间烟火与法治之光》中出场的关键人物,“扬孑”是该书原创作者,环环相扣的剧情主要讲述的是:本书以权威公开的社会治安个案为切入点,跳出对暴力案件的猎奇式呈现,转而站在社会全局视角,剖析案件背后潜藏的社会矛盾触点——如邻里纠纷、经济冲突、情感困境等如何从微小矛盾升级为极端事件,探寻个体行为失控与社会治理环节的深层关联。书中既聚焦司法机关的专业侦破过程,展现法治力量对社会秩序的守护;也深入探讨社区调解机制、心理干预服务、普法教育等社会支持体系在预防极端案件中的作用,反思当前社会治理中需完善的薄弱环节。最终以“个案警示—治理反思—价值倡导”为脉络,传递“尊重生命、理性沟通、依法维权”的核心价值观,倡导构建更具韧性、温度与协同性的社会治理体系,从源头减少极端事件发生,守护社会的平安与和谐。…
小说《人间烟火与法治之光》新书正在积极地更新中,作者为“扬孑”,主要人物有抖音热门,本文精彩内容主要讲述了:现实版“无双”:2021年广东跨境假币团伙覆灭记2021年深秋,广州白云机场的国际货运区,海关工作人员正在对一批标注“塑料玩具”的出口货物进行例行查验当开箱刀划开厚重的纸箱,露出的不是五颜六色的玩具,而是一沓沓用透明塑料袋包裹的“美元”——这些“美元”票面平整、纹路清晰,连水印都栩栩如生,若非专业人员,几乎无法分辨真假这场看似普通的查验,揭开了一个横跨中、缅、泰三国,涉案金额超2亿元的跨境假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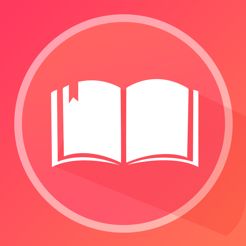
精彩章节试读
解离的灵魂:2018年南京“多重人格”弑亲案背后的人性迷局
2018年12月的南京,寒潮来得猝不及防,秦淮河畔的梧桐叶被冻得脆响,街头行人裹紧大衣行色匆匆。12月11日清晨7点,建邺区公安分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诡异的平静:“我杀了我妈妈,你们来抓我吧。”报警人叫林墨,22岁,南京某高校大三学生。当民警赶到林墨家时,玄关处的血迹从门口蜿蜒延伸到客厅,他的母亲张岚倒在卧室地板上,早已没了呼吸。而林墨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眼神空洞,嘴里反复念叨着:“不是我干的,是‘小雅’干的。”
这场看似普通的弑亲案,随着审讯的深入,逐渐暴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林墨声称自己身体里住着三个“人格”,而杀害母亲的,是其中一个名叫“小雅”的女性人格。这起案件不仅让“多重人格障碍”(解离性身份障碍)这个罕见的心理疾病进入公众视野,更让办案民警、心理专家陷入一场关于“真相与伪装疾病与罪恶”的艰难博弈。
一、诡异的案发现场:平静的凶手与矛盾的证据
民警抵达林墨家时,现场的景象与“弑亲案”应有的混乱格格不入。卧室里,张岚仰面倒在床边,颈部有一道整齐的致命伤口,凶器是掉落在一旁的水果刀——那是林墨从小用到大的一把刀,刀柄上只有林墨的指纹。客厅里,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牛奶,旁边摊开着一本《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书页停留在“解离性身份障碍”的章节,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批注,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像是两个人写的。
最反常的是林墨的状态。面对民警的询问,他既不惊慌也不抗拒,只是木然地配合。当被问到“为什么杀妈妈”时,他突然浑身一颤,声音瞬间变细,带着女孩的娇嗲:“不是我杀的,是‘小雅’!她讨厌妈妈总逼林墨学习,昨天晚上妈妈又骂林墨,‘小雅’就出来了……”说完,他又恢复了原本的声音,一脸茫然:“刚才……刚才是‘小雅’在说话吗?”
这种“切换人格”的诡异表现,让办案民警李涛心里打了个问号。从警15年,他见过形形色色的凶手,有故作镇定的,有崩溃大哭的,却从没见过像林墨这样“分裂”的。“是真的有心理疾病,还是为了脱罪装出来的?”李涛决定先从林墨的生活轨迹入手,寻找答案。
通过走访林墨的学校和邻居,民警了解到,林墨的成长轨迹充满了“矛盾”。他从小成绩优异,是邻居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但性格极其内向,几乎没有朋友,总是独来独往,书包里常年揣着一个旧布娃娃,说是“小雅的玩具”。张岚是一名中学教师,对林墨的要求近乎苛刻——每天必须学习到晚上11点,周末不准出门,甚至不允许他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有邻居反映,经常听到林墨家传来争吵声,张岚的声音尖利:“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而林墨的声音总是带着哭腔:“妈妈,我好累……”
更让民警在意的是,林墨的辅导员提供了一份关键线索:2017年,林墨曾因“情绪失控”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就诊,当时他告诉心理老师,“脑子里有个叫‘小雅’的女孩,会在他难过的时候出来陪他说话”。心理咨询室建议林墨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但张岚得知后,认为“心理咨询是浪费时间”,强行中断了他的咨询,还把他的布娃娃扔了——直到后来林墨偷偷找回来,布娃娃的一只眼睛已经掉了。
二、审讯室里的“人格切换”:三个灵魂的拉锯战
为了核实林墨是否真的患有多重人格障碍,专案组邀请了南京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赵伟参与审讯。2018年12月13日,第二次审讯在看守所进行,赵伟坐在审讯室的角落,全程观察林墨的反应。
审讯刚开始,林墨的状态很平静,回答问题条理清晰,能准确回忆起案发前一天的细节:“12月10日晚上,妈妈下班回来,看到我在看心理学的书,就发火了,说我‘不务正业’,还把我的书扔在地上。”说到这里,他突然捂住头,身体开始发抖,手指蜷缩成抓握的姿势,像是在抗拒什么。几秒钟后,他抬起头,眼神变得凌厉,语气也带着攻击性:“她凭什么扔林墨的书?林墨已经很努力了!我早就说过,再逼他,我就不客气!”
赵伟立刻追问:“你是谁?”
“我是‘阿哲’!”林墨的声音低沉了许多,与之前的“小雅”截然不同,“林墨太懦弱了,总是被欺负,我要保护他。昨天晚上,‘小雅’跟张岚吵架,张岚要打林墨,我没拦住‘小雅’,她就用刀捅了张岚……”
“阿哲”的出现,让案情更加复杂。根据林墨的表述,他身体里有三个人格:主人格“林墨”,性格懦弱、敏感,是从小被母亲严格控制的“乖孩子”;女性人格“小雅”,出现于10岁那年,当时张岚因为林墨考试没考第一,把他关在阳台罚站,“小雅”第一次出来,“陪他说话,帮他骂妈妈”;男性人格“阿哲”,出现于17岁,林墨被同学欺负时,“阿哲”突然出现,把欺负他的同学打伤,从此成为“保护者”。
为了验证这些人格的真实性,赵伟设计了一系列测试。他让林墨写下自己的生日,“林墨”写的是正确的日期;切换到“小雅”时,她写下的却是“6月1日”——那是林墨第一次得到布娃娃的日子;切换到“阿哲”时,他写下的是“9月15日”——那天林墨第一次反抗欺负他的同学。更关键的是,“小雅”害怕强光,每次审讯室的灯调亮,她就会尖叫着躲到桌子底下;而“阿哲”对疼痛不敏感,民警不小心碰到他的手,他毫无反应,直到切换回“林墨”,才会喊疼。
这些细节让赵伟初步判断,林墨的“多重人格”并非伪装。“真正的伪装者,很难在细节上保持一致,比如不同人格的生理反应、记忆断层,这些都是装不出来的。”但赵伟也强调,即使林墨真的患有多重人格障碍,也不能直接判定他“无罪”——根据《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才不负刑事责任。而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在某个人格主导时,是否“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需要更严谨的鉴定。
三、童年阴影:人格解离背后的“控制型母爱”
为了弄清楚林墨的人格解离是如何形成的,民警找到了林墨的父亲林建国。林建国常年在外地工作,与家人聚少离多,提起妻子和儿子,他满是愧疚:“我知道张岚对林墨太严了,但她总说‘为了孩子好’,我劝过几次,她不听,我也就没再多管……”
从林建国提供的家庭照片和日记里,民警拼凑出林墨痛苦的童年。林墨3岁时,张岚就开始教他背古诗、算算术,只要他表现出一点懈怠,就会被关在房间里“反思”。5岁那年,林墨因为把玩具弄坏,被张岚罚跪了两个小时,直到林建国回家才被解救。10岁时,林墨第一次考试没进班级前三,张岚把他的布娃娃(那是林建国出差买给林墨的礼物)扔到楼下,还说“只有废物才玩玩具”——也就是那天晚上,林墨第一次出现了“小雅”的人格,他在日记里写道:“今天脑子里有个姐姐,她告诉我,她会保护我,不让妈妈欺负我。”
初中时,林墨的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但张岚的要求越来越高。有一次,林墨因为感冒发烧,月考成绩掉到了第五名,张岚拿着成绩单,在客厅里骂了他两个小时,还扇了他一耳光。那天晚上,林墨用美工刀在手臂上划了几道口子,日记里的字迹变得潦草:“妈妈不喜欢我了,我好害怕……‘阿哲’说,他会帮我变得强大,再也不让人欺负我。”
这些童年创伤,正是多重人格障碍的重要诱因。赵伟解释:“解离性身份障碍的核心是‘心理防御机制’的过度启动。当个体遭遇无法承受的创伤(比如长期的虐待、控制、忽视)时,为了保护自己,大脑会将‘自我’分裂成不同的人格,让不同的人格去承受不同的痛苦——比如‘小雅’承受委屈和愤怒,‘阿哲’承受恐惧和反抗,而主人格‘林墨’则可以继续维持‘正常’的生活。”
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还发现一个令人心碎的细节:案发前一周,林墨拿到了某名牌大学的保研资格,他本来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却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张岚跟同事打电话:“林墨那点成绩算什么?必须考博,不然以后没出息!”就是这句话,成了压垮林墨的最后一根稻草。案发当晚,张岚又因为林墨“看心理学书”发火,甚至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小雅”突然出现,夺过水果刀,刺向了张岚。
四、鉴定与审判:法律如何面对“解离的灵魂”
2019年1月,南京市精神卫生中心对林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法定精神鉴定。鉴定过程中,专家团队采用了“人格访谈记忆测试脑电波监测”等多种手段,最终得出结论:林墨患有“解离性身份障碍”,案发时,主导他行为的是“小雅”人格,且“小雅”人格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这个鉴定结果引发了巨大争议。张岚的家人无法接受:“就算他有心理疾病,也不能随便杀人!难道我妹妹的命就白丢了吗?”而林墨的父亲林建国则陷入了痛苦的挣扎:“我知道张岚有错,但林墨也很可怜……他不是故意的,是病了啊。”
办案民警李涛也感到棘手:“从情感上,我们同情林墨的遭遇,但从法律上,我们必须尊重鉴定结果。不过,即使他不负刑事责任,也需要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直到他的病情稳定,不会再对社会造成危害。”
2019年3月,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法庭上,林墨大部分时间处于“林墨”人格状态,当听到法官念出“张岚的死亡鉴定报告”时,他突然崩溃大哭:“妈妈,对不起……我不该让‘小雅’出来的……”而当“小雅”人格出现时,她对着原告席大喊:“是她先逼我们的!她从来没爱过林墨,她只爱成绩!”
最终,法院根据精神鉴定结果和相关法律规定,判决林墨不负刑事责任,但需送往南京市精神病院接受强制医疗,期限为两年。判决生效那天,林建国去精神病院看林墨,林墨抱着布娃娃,眼神恢复了些许清明:“爸爸,我会好好治病,等我好了,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林建国看着儿子,泪流满面,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个完整的家,早就随着张岚的死亡和林墨的疾病,碎得再也拼不回来了。
五、案件背后的反思:被忽视的“心理求救信号”
林墨案虽然尘埃落定,但它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在这起案件中,有太多被忽视的“心理求救信号”:林墨10岁时出现“小雅”人格,17岁出现“阿哲”人格,2017年主动去学校心理咨询室求助,这些都是他向外界发出的“求救信号”,却被母亲张岚一次次无视。张岚的“控制型母爱”,看似是“为孩子好”,实则是将自己的焦虑和期望强加在孩子身上,最终将孩子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赵伟医生在后续的采访中提到:“现在很多家长都存在‘过度控制’的问题,他们把‘成绩’‘成功’当成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却忽视了孩子的心理需求。其实,孩子的心理健康比成绩更重要——一个心理健全的孩子,即使成绩不是顶尖,也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一个心理扭曲的孩子,即使成绩再好,也可能在某个瞬间,被压力压垮,做出极端的事情。”
此外,林墨案也让“多重人格障碍”这个罕见疾病得到了更多关注。在此之前,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停留在电影《分裂》等影视作品中,认为它是“装出来的很诡异”。但事实上,多重人格障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心理疾病,患者往往是童年创伤的受害者,他们需要的不是歧视和恐惧,而是理解和治疗。
如今,林墨在南京市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已经三年多了。据医生介绍,他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人格切换”的频率越来越低,大部分时间能保持“林墨”人格的稳定,还学会了通过画画、写日记来疏导情绪。有时候,他会在日记里写:“希望以后再也没有‘小雅’和‘阿哲’,我想做一个完整的林墨,好好活着,替妈妈看看这个世界。”
南京的秦淮河依旧流淌,每年冬天,还是会有寒潮来袭。但对于林墨、林建国和张岚的家人来说,那个2018年的冬天,永远是他们生命中无法愈合的伤口。这个案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家庭教育中的误区,也照出了社会对心理健康的忽视。愿这个悲剧能警醒更多人: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尊重每个人的“自我”,别让“爱”变成伤害,别让“期待”变成压垮灵魂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