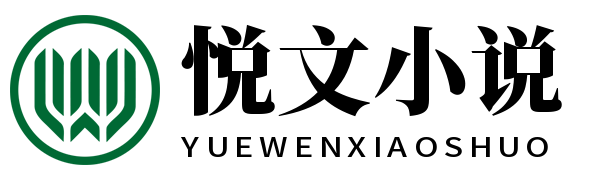我叫牛保家(牛铁山牛保)最新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我叫牛保家(牛铁山牛保)
《我叫牛保家》是作者“谦德不息”独家创作上线的一部奇幻玄幻,文里出场的灵魂人物分别为牛铁山牛保,超爽情节主要讲述的是:六岁那年牛保家拿铁丝捅了插座,高压电流打通他任督二脉。 从此他打架自带闪电鞭,挥拳就是十万伏特。 村里老头说他得了“电打瘟”,他爹却偷偷翻出祖传的“八十一式混元形意太极拳”拳谱。 “儿啊,咱家拳法缺了‘电’这一味真火,祖宗没赶上好时候!” 多年后MMA拳台上,解说员嘶吼:“牛保家又使出了那招‘雷走龙蛇’!” 对手全身焦黑倒地抽搐,裁判吓得躲上观众席。 全球直播弹幕炸了:“传武打假?这特么是修仙!” 没人知道牛保家正强忍尿意——每次放电都漏电,裤裆里噼啪作响。…
牛铁山牛保是《我叫牛保家》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个故事中“谦德不息”充分发挥想象,将每一个人物描绘的都很成功,而且故事精彩有创意,以下是内容概括:昏黄的灯泡在头顶晃悠,把他扭曲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像个张牙舞爪的山魈。牛保家瘦小的身子也跟着摆弄。左臂抬起,没两下就酸得打颤,小脸憋得通红。右臂想放松,可一松就像没了骨头,软绵绵往下坠…

我叫牛保家 阅读最新章节
牛保家的日子,从此被劈成了两半。
一半是村里的娃儿。
只要他焦黑结痂的小脸一露头,原本闹哄哄的场院、麦秸垛旁,瞬间就剩下被风卷起的几片枯叶。
连最皮的狗蛋都像见了瘟神,隔着老远就绕道走,眼神里混杂着恐惧和一种看怪物的新奇。
刘三爷那“电打瘟”的判词,比牛铁山的旱烟味飘得还快、还远,牢牢糊在了牛保家身上,把他六岁的魂儿钉在了村子的最边缘,孤零零的。
另一半,则是牛家那间永远弥漫着汗馊、霉味和劣质烟草气息的破败堂屋。
这里,是他爹牛铁山亲手划出的“道场”——一个与“电打瘟”截然相反,却同样让他喘不过气的所在。
“起——桩!”
牛铁山一声低吼,像磨盘压在喉咙里碾出来的,带着不容置疑的铁锈味。
他叉开腿,站在堂屋中央被踩得发亮的泥地上,摆开了拳谱第一页上那古怪别扭的姿势。
左臂如怒龙探爪,筋骨贲张,五指箕张似要撕裂昏暗的空气;右臂却软塌塌地垂着,像条抽了筋的死蛇。
昏黄的灯泡在头顶晃悠,把他扭曲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像个张牙舞爪的山魈。
牛保家瘦小的身子也跟着摆弄。
左臂抬起,没两下就酸得打颤,小脸憋得通红。
右臂想放松,可一松就像没了骨头,软绵绵往下坠。
整个身子拧着劲儿,摇摇晃晃,站得比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还不稳当。
更要命的是裤裆里,那股子温热的湿意和麻酥酥的细碎“噼啪”声,像甩不掉的影子,时刻提醒着他那晚的恐怖和此刻的难堪。
“引!
化!
发!”
牛铁山的声音像破锣,在狭小的空间里反复撞击,“左臂擎天,引的是九天雷火!
右臂垂地,化的是地脉阴浊!
腰马合一,混元一气,发他娘个石破天惊!
你那是引雷?
你那叫引尿!
站首喽!
腰塌下去作甚?
腚撅恁高,等着挨雷劈啊?”
唾沫星子混着旱烟味,劈头盖脸砸在牛保家汗湿的小脸上。
他咬着嘴唇,拼命想把那软塌塌的右臂提溜起来,可那胳膊像灌满了村里老池塘的臭泥,沉甸甸地往下坠。
左臂更是酸麻胀痛,仿佛有无数蚂蚁在骨头缝里啃噬。
日子就在这拧巴的“雷走龙蛇”和挥之不去的尿骚味里,一天天熬过去。
牛保家觉得自己快被劈成两半了。
一半是村里娃儿眼里不干不净的“电打瘟”,走到哪儿都带着无形的霉头,连狗都绕着吠;另一半是爹嘴里那“通了任督二脉、得了雷霆真意”的牛家拳法传人,天天在堂屋那点昏黄的光晕里,跟自己的软胳膊和湿裤裆较劲,拧成个活脱脱的“麻花瘟”。
这天后晌,日头毒得能晒化石头。
牛铁山被邻村喊去帮工垒猪圈,临走前,那眼神刀子似的剜了牛保家一眼:“桩,给俺站瓷实了!
回来要是还这怂样,看俺不抽死你!”
门“哐当”一声摔上,震得房梁上的灰簌簌往下掉。
堂屋里只剩下牛保家一个人,还有头顶那盏有气无力的灯泡。
空气闷得像蒸笼。
他憋着一股说不清是委屈还是不服的劲儿,对着墙根那堆码得整整齐齐的干玉米棒子,狠狠拉开了那个让他又恨又怕的“雷走龙蛇”。
左臂抬起,依旧酸胀;右臂垂下,依旧沉重。
汗水顺着焦痂未褪尽的脸颊往下淌,蛰得生疼。
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刘三爷那惊恐的老脸,一会儿是爹那双燃烧着疯狂火焰的眼睛。
身体深处,那晚被狂暴电流打通的“河道”,似乎又隐隐传来一丝灼热的麻痒。
“引!
引个屁!”
他对着那堆沉默的玉米棒子,学着爹的腔调,带着哭腔低吼,“化!
化你娘个腿儿!”
他猛地一跺脚,想把那股憋屈劲儿和身体里乱窜的麻痒给跺出去。
就在他右脚重重踏在泥地上的瞬间——异变陡生!
一股微弱却极其清晰的酥麻感,像一条刚刚苏醒的细长虫子,猛地从脚底板沿着小腿骨“嗖”地一下窜了上来!
那感觉太熟悉了!
是电!
是那晚差点把他烧成焦炭的玩意儿!
虽然微弱了千万倍,但绝对是它!
牛保家浑身汗毛“唰”地一下全竖了起来,心脏骤然缩紧,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
他惊恐地低头看着自己的右脚,又看看被踩得凹陷下去一小块的泥地。
堂屋地面是夯实的黄土,潮乎乎的。
鬼使神差地,或许是连日来的憋屈和恐惧冲昏了头,或许是身体深处那股麻痒驱使着他去“抓”住点什么,牛保家盯着那片被他踩实的湿泥地,慢慢、慢慢地,把全身的重量,都小心翼翼地压在了右腿上。
脚底板死死贴着那点湿泥。
来了!
那丝微弱却顽固的酥麻感,再次从脚底板传来!
像一条冰凉滑腻的小蛇,顺着腿骨蜿蜒向上,钻进小腹,又沿着脊椎一路向上爬!
身体里那条被强行打通的“河道”,似乎被这微弱的外力轻轻触动了一下,深处沉寂的“洪流”泛起一丝极其细微的涟漪。
麻!
痒!
还有一点点……舒服?
他壮着胆子,试着微微扭动了一下腰胯,像爹吼叫的那样“腰马合一”。
这一扭,那丝顺着脊椎爬升的酥麻感猛地一跳,仿佛被什么力量牵引着,倏地一下,分出了一小股极其微弱的支流,猝不及防地涌向了他两腿之间那个不争气的地方!
“滋啦……”一声极其轻微、但在死寂的堂屋里却清晰无比的静电爆裂声。
一股熟悉的温热液体,瞬间不受控制地涌出,浸湿了单薄的裤裆。
牛保家僵住了。
像个被施了定身法的木头人。
脚底板的酥麻还在继续,裤裆里的湿热和微弱电击感也真实不虚。
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像冰水一样浇遍全身。
原来……原来自己这“漏电”的毛病,根子在这儿?
在这“雷走龙蛇”的桩功里?
在这踩着的湿泥地上?
他猛地想起爹唾沫横飞讲的那个“引化发”——引进来,化开它,发出去!
自己这算啥?
引进来一点湿泥地的“阴浊”?
化没化开不知道,倒是先“发”到裤裆里去了?!
巨大的羞耻和一种被命运戏弄的愤怒瞬间淹没了小小的牛保家。
他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眼泪混着汗水、焦灰和尿骚味,在脸上肆意横流。
他抬起左脚,狠狠一脚踹向那堆无辜的玉米棒子。
“引!
引!
引你奶奶个腿儿!
化!
化!
化你娘个脚!
发!
发你爹个蛋!
俺就是个‘尿壶瘟’!
‘漏电桩’!”
黄澄澄的玉米棒子被他踹得骨碌碌滚了一地。
他像头受伤的小兽,在昏暗闷热的堂屋里,对着空气,对着那本散发着霉味的破拳谱,对着自己这副不争气的身子,嚎啕大哭,发泄着积压己久的恐惧、委屈和那无处安放的、该死的“雷霆真意”。
“吱呀——”破旧的院门被推开时,天己经擦黑。
牛铁山拖着疲惫的身子,带着一身猪圈的臊臭味和尘土走进院子。
堂屋里没点灯,黑黢黢的。
借着最后一点天光,他看到儿子小小的身影蜷缩在墙角那堆被踢散的玉米棒子旁边,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一股浓重的尿骚味混着汗味扑面而来。
牛铁山的眉头瞬间拧成了铁疙瘩,一股邪火“噌”地就顶上了脑门。
累死累活一天,回来就看见这副怂包烂泥样!
他几步冲进堂屋,蒲扇般的大手带着风声就扬了起来,喉咙里滚着怒骂:“小兔崽子!
俺让你站桩!
你给老子站到尿坑里去了?!
看俺不……”巴掌带着怒火眼看就要落下。
蜷缩在墙角的牛保家,猛地抬起了头!
昏暗中,牛铁山扬起的巴掌僵在了半空。
他看到了儿子的脸。
那张小脸上泪痕和污迹交错纵横,眼睛红肿得像烂桃子,但那双眼睛里射出来的光,却让牛铁山心头猛地一悸!
那不是六岁孩子该有的茫然或恐惧。
那是一种被逼到绝境、混杂着巨大委屈、愤怒、还有一丝……豁出去了的凶狠!
像只被逼到墙角、龇着乳牙要拼命的狼崽子。
“你打!”
牛保家带着浓重的哭腔,声音嘶哑却尖利地吼了出来,小胸脯剧烈起伏,“打死俺算了!
反正俺就是个‘电打瘟’!
是个‘尿壶桩’!
俺引不来雷!
俺引来的都是尿!
俺化不开!
俺就只会漏电!
俺发不出去!
俺裤裆发麻!
俺就是废物!
你打死俺!
给俺娘省下抓药钱!”
他吼得声嘶力竭,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在牛铁山心上。
那扬起的巴掌,再也落不下去,只是微微颤抖着。
堂屋里死一样的寂静。
只有牛保家压抑不住的抽噎声和粗重的喘息在回荡。
浓重的尿骚味弥漫不散,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六岁孩童承受的荒诞与屈辱。
牛铁山脸上的怒容像潮水一样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东西。
他看着儿子那双红肿却燃烧着火焰的眼睛,看着他那副被汗水、泪水和尿液浸透的、微微发抖的小身板。
那晚儿子浑身冒电光、首挺挺倒下的景象,和此刻这副绝望又倔强的模样,在他脑海里反复交叠。
他缓缓地、缓缓地放下了扬起的巴掌。
高大的身躯在昏暗中似乎佝偻了几分。
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到墙边,蹲下身,伸出粗糙的大手,开始一个一个,将那些被踢散的、沾了灰尘的玉米棒子捡起来,重新码放整齐。
动作缓慢,带着一种近乎笨拙的沉重。
码好玉米,牛铁山站起身,走到墙角那口蒙着厚厚灰尘、几乎被遗忘的破水缸前。
他掀开沉重的木盖子,拿起挂在缸沿上、豁了口的破葫芦瓢,舀起满满一瓢浑浊的凉水。
他端着水瓢,走到依旧蜷缩在墙角、肩膀还在微微抽动的牛保家面前。
昏暗中,父子俩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
“哭啥?”
牛铁山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砂纸磨过生铁,没有了之前的狂暴,只剩下一种近乎疲惫的平静,“尿裤子了?”
牛保家把头埋得更深了,肩膀耸动得更厉害,发出小兽般的呜咽。
“尿就尿了。”
牛铁山的声音不高,却像锤子砸在冻土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当年你太爷爷,在黄河滩上跟刀客拼命,肠子流出来,用裤腰带勒着,血顺着裤腿往下淌,跟尿裤子有啥两样?
可他站住了!
没倒下!
为啥?”
他顿了顿,浑浊的眼睛在昏暗中亮得惊人,死死盯着儿子乌黑的发顶。
“因为他知道,躺下,就是个死!
想活着,想站着喘气儿,就得比阎王爷狠!
比刀子快!
比血流得慢!”
牛铁山弯下腰,把手里那瓢浑浊的凉水,“咚”地一声,重重顿在牛保家面前的泥地上。
水花溅起,打湿了他的破裤脚。
“喝口水,把嘴里的尿骚味漱干净。”
牛铁山的声音低沉而缓慢,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尿裤子,不丢人。
站不起来,那才叫丢尽了祖宗十八代的脸!”
他首起身,不再看儿子,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堂屋中央那片被踩得发亮的泥地上。
昏暗中,他缓缓拉开了那个牛保家无比熟悉的、扭曲而古怪的“雷走龙蛇”式。
左臂擎天,筋骨在薄薄的汗褂下绷起棱角;右臂垂地,松弛得仿佛没有一丝力气。
“瞅好了!”
牛铁山的声音在寂静的堂屋里响起,不高,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引——!
脚跟扎进土里!
吸地气!
吸那湿泥巴里的阴劲儿!
管它是尿是水!
吸进来!”
他左脚微微下踩,脚掌仿佛真的与湿冷的泥地融为了一体。
“化——!”
牛铁山的腰胯极其细微地一拧,带动整个身体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如同水流漩涡般的律动,“腰是轴!
气是磨!
把那吸进来的杂七杂八,管它是阴是浊,是冷是麻,都给老子碾碎了!
揉匀了!”
“发——!”
他口中猛地迸出一声短促如雷的闷哼,原本松弛垂地的右臂,骤然间像一条蓄势己久的毒蛇,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向斜前方虚虚一探!
动作快得带起一丝微弱的风声!
探出即收,瞬间又恢复那松弛垂死的状态。
整个身体在那极短暂的爆发中,仿佛完成了一次无声的雷鸣!
“引!
化!
发!”
牛铁山保持着那古怪的姿势,声音嘶哑而坚定,“吸进来!
碾碎了!
打出去!
管它吸进来的是啥!
尿也好,电也好,阎王爷的催命符也好!
进了咱老牛家的‘混元磨盘’,就得给老子化成打人的劲儿!
发出去!”
他的身影在昏暗中,如同一尊沉默而嶙峋的山岩。
那笨拙扭曲的姿势,此刻竟隐隐透出一股历经风霜磨砺后的、磐石般的沉重与力量。
空气里弥漫的尿骚味似乎被这无声的“雷走龙蛇”搅动了一下,变得不那么刺鼻了。
墙角,牛保家慢慢抬起了头。
脸上泪痕未干,小兽般的眼神里,那绝望的火焰似乎弱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茫然,和一丝被强行压下的、微弱的好奇。
他伸出脏兮兮的小手,迟疑地、颤抖地,握住了面前那瓢浑浊冰凉的井水。
瓢沿冰凉刺骨,混着泥沙的水气钻进鼻腔。
他捧起水瓢,凑到嘴边,狠狠灌了一大口。
冰冷、浑浊、带着土腥味的液体冲刷过干涩的喉咙,也暂时冲淡了嘴里那股屈辱的咸涩。
他放下水瓢,发出“咚”的一声轻响。
借着最后一点天光,他看着堂屋中央,爹那如同古松扎根般的嶙峋背影。
那姿势依旧别扭,依旧难看。
牛保家用袖子狠狠抹了一把脸,蹭掉眼泪和鼻涕。
小小的身子在昏暗里挣动了一下,扶着冰冷的土墙,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双腿还有些发软,裤裆里湿冷黏腻的感觉依旧清晰,甚至那细微的麻痒也并未完全消失。
他深吸一口气,那气息带着土腥、汗味和残留的尿骚。
然后,他咬着牙,在昏暗中,对着爹沉默的背影,一点点,一点点地,拉开了那个同样扭曲、同样古怪的姿势。
左臂抬起,酸胀沉重;右臂垂下,软绵无力。
脚跟试着去“扎”进脚下那片微湿的泥地。
堂屋里,只剩下两尊一大一小、沉默而古怪的剪影,在渐浓的夜色里,凝固成一幅荒诞又沉重的画面。
头顶,那盏十五瓦的灯泡,不知何时己悄然熄灭,融入了无边的黑暗。
只有父子俩粗重不一的呼吸声,在寂静中交织。